2025年的夏天比往年夏天更漫长,彷佛季节向我们多馈赠了一些热烈的时光。但愿这不是我的错觉。
夏天结束前,我在南京办了一场聚会。来自中原的老魏,来自浙江的老杜,和我数日把酒言欢,难舍难分。上一次我们仨聚齐,还是二十二年前,在南京的一个小酒馆里。那时,老魏是小魏,老杜是小杜,我们的手机铃声还是“前度刀郎”的歌。
我开车到南京南站接老杜前,他特意描述了一下自己“老去”的样子,提醒我不要“直把小杜当老杜”。搞得我都有点紧张了,好在眉眼之间还是当年模样,“接头”并无差池。
30多年前,我们仨同在中原当兵。虽不在同一个部队,但有幸同时在一家报社实习过。我们瞬间感觉到是一类人,就此走到一起。那些年,在我和妻子租住和新买的房子里,我们仨吃着炒菜、打着地铺,只觉灯火可人、老酒暖屋。我们喝过的酒,有些还是开店的岳父岳母“赞助”的。
后来老魏也成家了,家就安在洛河边。我们仨饮罢杜康,站在屋外,面对着河水、星光和人家灯光,许着不切实际的愿望。譬如,哥几个就在这个古老的城市里打出一片天地,就此不分离。人间草木,彼此依托,想来是最好的景致。
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二字头的年龄,内心里的江湖遥远而辽阔,很多事都可以拿来预测或寄望。
有一年的平安夜,我们结伴去看了一场演出。出得场馆已是凌晨,走在龙鳞路上,路灯在寒风中愈显稀落。老杜和老魏小声哼起“你快乐吗,我很快乐……”,不意就此停不下来,老杜还跳起了舞。我和妻子看着他们的“表演”掩嘴而笑。还有一回,冬日里,我们买了羊肉,坐了很久的车,到黄河边整了一场“烧烤大会”。时隔多年,妻子依然对这两个场景念念不忘。
后来老杜也谈了对象,带到我家吃饭。我和妻子、老魏都觉得姑娘人不错,说些早日结婚生子的吉利话。倘日后三家人常来常往,我们也就在这座千里之外的异乡扎了根,得了一份慰藉。那时老杜进了我们曾经实习过的日报社,做了记者,成了我和老魏羡慕的对象。
烟花易冷,诺言易碎,也就几年工夫,我们就散了。我回到故乡南京工作,和我是同乡的老魏留在中原,守望一份挚爱的事业,而老杜则远赴海边城市,“到了天边边”,离他的河北老家更远了。他和那位姑娘终究成了“故事”。这似乎是人世间的一种必然。
二十二年间,我们多次计划过重聚一次,但每每被变化打破计划。其间,我和老杜换了“东家”,老魏也一度定居重庆。有时我会莫名心生畏惧,觉得各自家事和公事缠绕,江湖日远,再想“说走就走”太难了。
老杜对重聚一事最是心思潦草,几次三番地在微信里说:“几个老家伙,一脸的褶子,有啥好见的,还不如留个年轻时的美好印象,在电话里追忆逝水年华。”最过分的是,十多年前,他来南京公干,上了我所在的大楼,却直到离开南京才告知我,他来过。
转机是老魏带来的。他儿子在今年夏天考上了上海的知名大学,他和母亲、妻子要送孩子到上海。我便提议,我们仨在南京见一面。我本担心老杜推托,然而他欣然答应,且专门调了班来。也许,人生进入下半场的最大标志,就是儿女之事成了决定性的契机。
聚会的那晚,我和妻子在古色古香的老门东设宴款待。收到包间信息后,老杜立马反对:“像当年一样找个苍蝇馆子就完事,何必多花钱!”老魏也认为吃什么不重要,随意点就好。我只告诉他们,此地最是怀旧,他们便不再坚持。
当晚,我喊上岳父,还有妻妹一家四口。见面的那一刻,一群“老熟人”手握了又握,老杜连连感慨妻妹从一个小丫头片子变成了中年人。那晚我如有神助,喝了超量的酒也没醉。饭前大家都说少喝点,结果把带去的酒都喝完了,连襟又从下单叫了酒来,这才尽兴。
吃罢,老魏和老杜在我家又打上了地铺。我们彻夜长谈,相约此后每年一聚。客厅的电视机关着,大屏幕像镜子一样映着我和老魏的半头白发,和老杜所谓的“一脸褶子”。我们已年过半百,飘蓬落定,当年行而未至、舞而未了的“远方”,早已淹没在票根和一路烟尘中。
在茶香四溢、昔日重来的瞬间,突然觉得,江湖也没那么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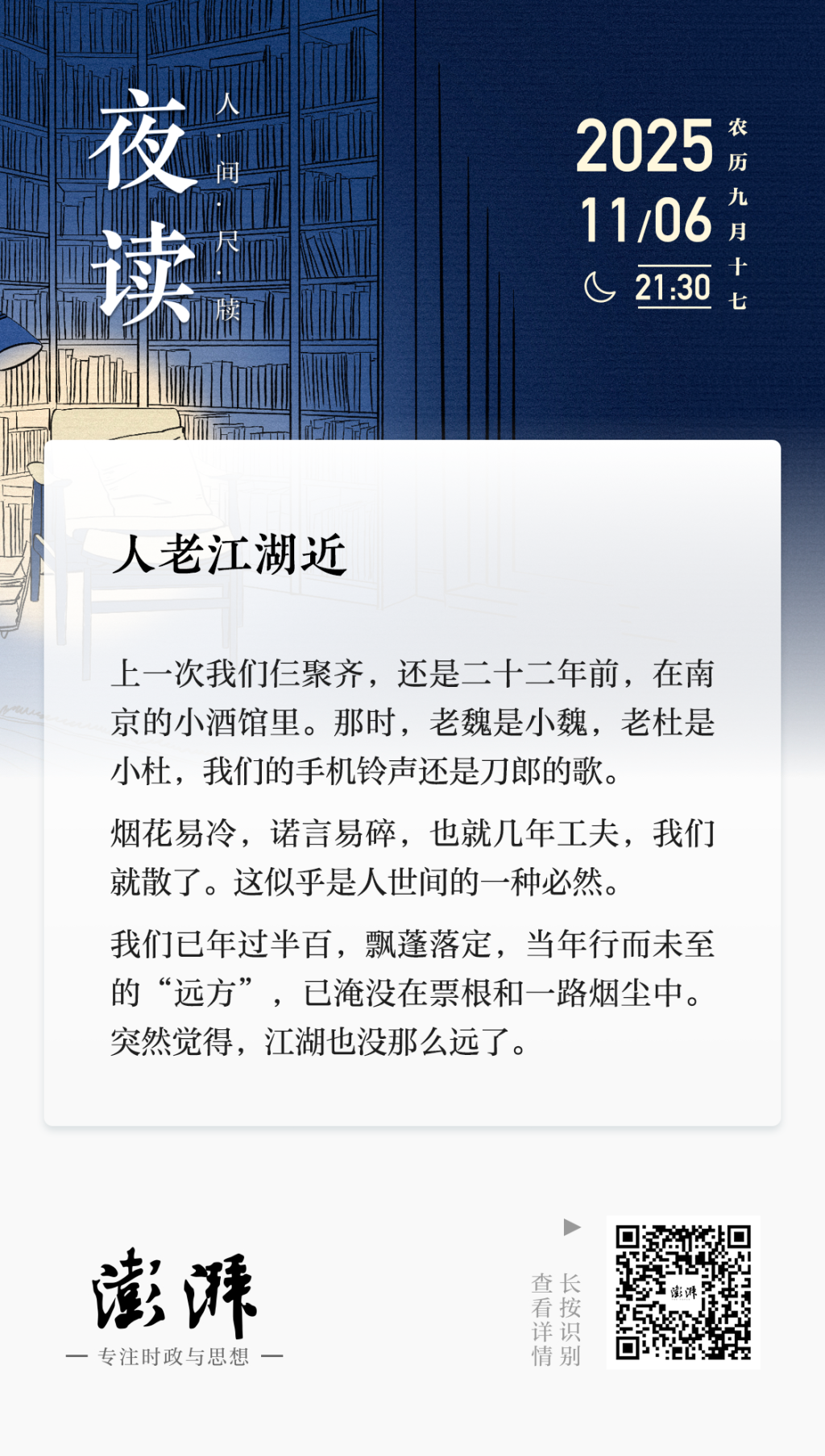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