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临终之前,苏格拉底直截了当地打发走了自己的妻子克珊西佩,表示自己希望在男性朋友们的陪伴下死去。这一戏剧化的夸张情节反映出了那个时代夫妻之间的感情距离。丈夫与妻子之间的疏远也延伸到了其他领域。雅典的男性和女性各自过着不同的社会生活,而我们手头的大部分信息都是关于男性的。一个似乎容易一点的处理办法是去描述男性的生活,然后轻描淡写地声称,女性并未参与其中的大部分事务。
萨拉·波默罗伊在《女神、娼妓、妻子与女奴:西方古典时代女性的社会生活》中的这段描述,反映了古希腊时期男女生活的“距离感”。
说起古希腊,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宏大的神庙和可供演讲、集会之用的广场,这些公共空间支撑着古希腊人的生活、制度乃至文明,但如果严谨一点,或许将“古希腊人”改为“古希腊男性”更为恰当。正如萨拉·波默罗伊在书中所言:“男女有别在空间上得到了强调。男性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会待在公共场所,如集市上或体育馆里;受人尊敬的女性则待在家里。与男性逗留徘徊其中的富丽堂皇的公共建筑相反,雅典古典时代的私人住宅通常是阴暗、肮脏、有害健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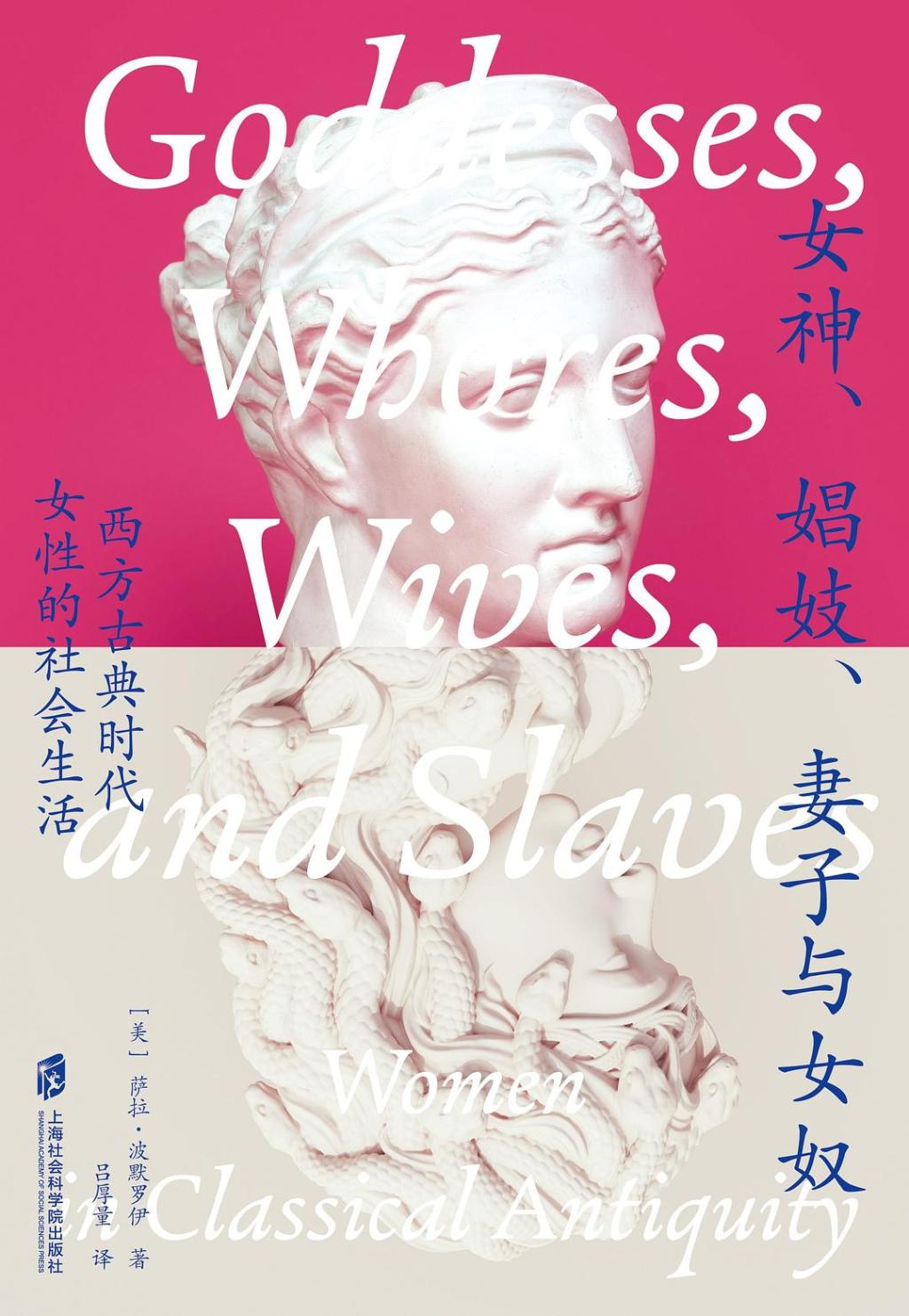
《女神、娼妓、妻子与女奴:西方古典时代女性的社会生活》
女性之所以待在家里,不仅仅是因为她们的工作性质没有提供多少外出的机会,还因为受到了公共舆论的影响,以及家庭、丈夫与孩子种种需求带来的束缚。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璀璨中,从哲学到政治、文学到法律、艺术到建筑,无数男性留下赫赫之名,女性却属于被遮蔽的群体。萨拉·波默罗伊用“女神、娼妓、妻子、女奴”这四个身份,揭示男性主导的社会对女性群体的刻板印象与功能划分,并进一步探求这四类角色的真实生活。从奥林波斯山上的女神、上层阶级的贵妇、宗教仪式中的女祭司与贞女、深居简出的雅典女性到处境艰难的底层女性,她重建了一个完整而鲜活的古代女性世界。
传说中的海伦,就是女性被污名化的象征
“女神、娼妓、妻子、女奴”这四个身份,之所以被萨拉·波默罗伊视为男性视角的刻板印象与功能划分,是因为它并不能真正诠释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和作用。或者说,这几个身份只是男性在权力导向之下为女性安排的“工作”,而且它们看似大相径庭,实际上却都服务于男性利益,意在垄断女性身体的定义权和分配权,原本多元的女性个体被脸谱化。
英国学者贝塔妮·休斯则在《特洛伊的海伦:女神、公主与荡妇》一书中提供了另一个角度:有些女性身兼几种身份,但这恰恰更意味着污名化。作为古希腊最知名的女性,海伦是女神,也被斥为娼妓,她是妻子,但从她的困境来看,说是男性争夺的女奴也不为过。
大仲马在《巴黎的莫西干人》中曾写道:“每个案件都有一个女人;每一次他们提交报告,我都会说:‘寻找那个女人。’”这句话颇有“红颜祸水”的意味,可它显然不是历史和社会的真相。女性的行为往往会在历史事件和社会事件中被放大,海伦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那个女性通常被剔出历史的时代,她却以反面形象被载入史册。几千年来,海伦都是美貌的象征。《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面世标志着西方的人们首次意识到个人道德的观念正经受考验,海伦是这一拷问的关键,因为她本身就是个难解之谜。“作为一名美得炫目且感情上并不诚实的王后、一枝引发数十年灾难的出墙红杏,她却完好无损地活了下来。她是神秘的混合体,兼有固执和敏感、智慧和本能、脆弱和强大。在她出生的年代,善恶的界限并不分明,因此她两者兼具。她拥有完美的肉体,然而这完美的肉体却酿成了灾难。她无疑充满危险,但男人们依然忍不住爱上她。她是作为一个不甘心只当花瓶的女性被载入史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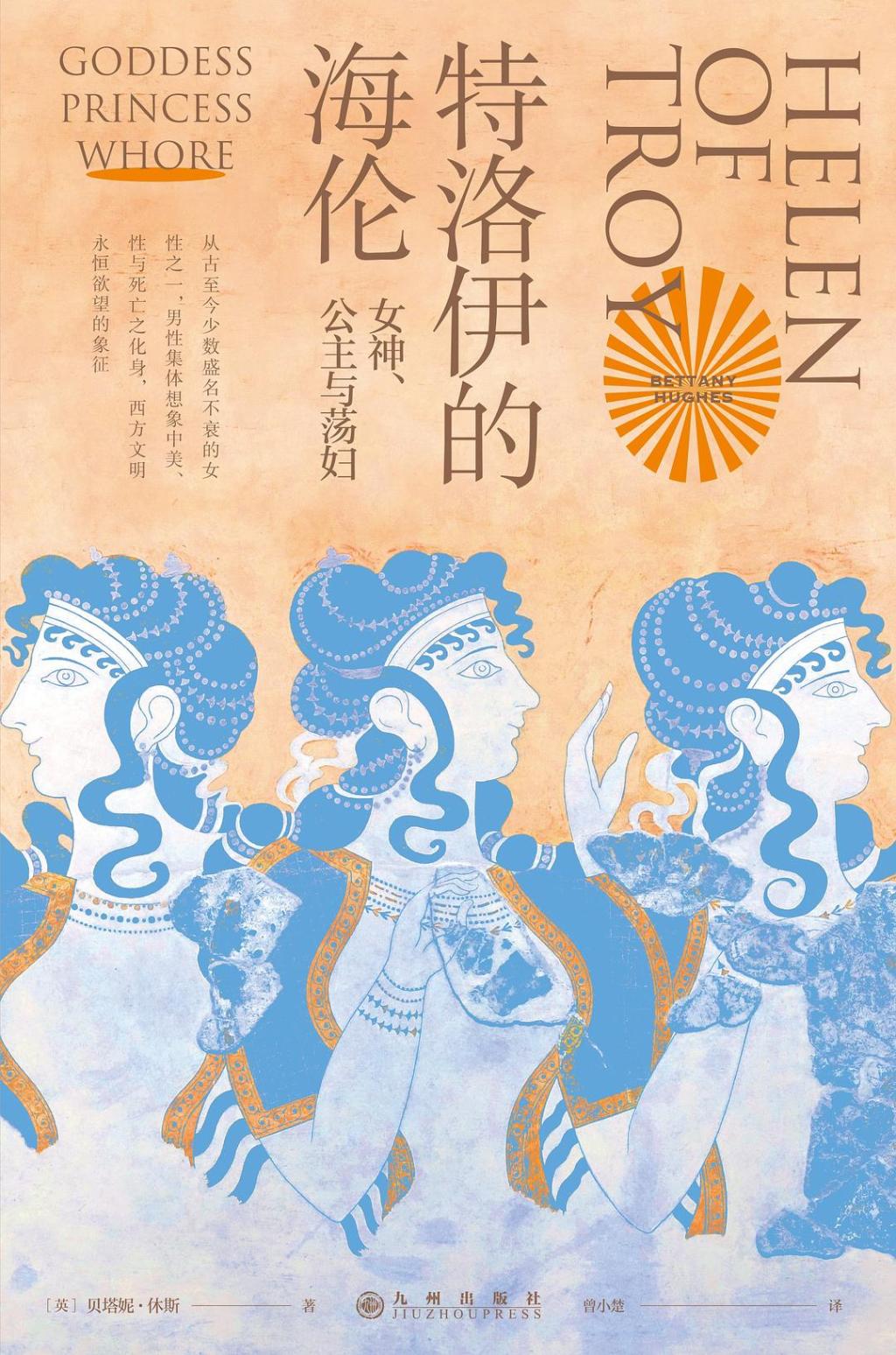
《特洛伊的海伦:女神、公主与荡妇》
当然,荷马刻画的海伦并不完整。《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只描写了海伦的一部分故事。其他已经失传的史诗补充了海伦的故事,但它们可能只剩下零星片段甚至仅有书名。不过它们还是合力贡献了海伦在西方文化里的无数形象:少女、王后、祭司、妓女、鬼魅、精灵……这些都是男性欲望的投射。
事实上,历史上的权力斗争和战争主角多半是男性,但导火索往往被推给女性。正如歌德所写的那样:“把女神变成女巫、把处女变成荡妇都毫无技巧可言,但是如果倒过来,要把被人鄙视的变得有尊严,把堕落的变得受人欢迎,那就需要技巧或者性格了。”相比海伦,萨拉·波默罗伊在《女神、娼妓、妻子与女奴》中书写的那些普通女性,没有倾国倾城的美丽,也不会成为传说,却同样是男性的附庸。萨拉·波默罗伊这样描绘古希腊男性:“我们有情妇可供消遣,有女仆服侍自己,还有妻子生育合法子嗣。”海伦这样的“红颜祸水”,只能存在于传说中,而在当时,古希腊社会对女性定义的“出路”,可以在古希腊神话的女神当中找到模板。
萨拉·波默罗伊写道:“对父权制社会来说,最方便适宜的做法是在不同的女性身上寻求不同的理想特质,而不是在一个人身上满足全部需求。……个性全面发展的女性容易引起缺乏安全感的男性的焦虑。从古至今,无法与集众多天赋于一身的女性共处的男人们,将女性设想为‘非此即彼’的不同角色。女性仍在为三者必择其一的选择而苦恼:要么成为雅典娜——聪慧但缺乏性魅力的职业女性;要么成为阿佛洛狄忒——轻佻的性工具;要么成为赫拉那样受人尊敬的妻子与母亲。”但在事实上,雅典娜不需要男人,并不能说明她是独立女性,只是男性在造神过程中剥夺了她的性欲和情感。阿芙洛狄忒则完全被物化,失去了女性自身的复杂性。赫拉更为凄惨,她恪守忠贞,可宙斯却始终滥情。
古希腊和古罗马女性并非全然被动
在萨拉·波默罗伊提出的三条路径中,最值得玩味的是“雅典娜——聪慧但缺乏性魅力的职业女性”。这说明女神在神话中也受制于父权神系的秩序,但更重要的是,古希腊女性多少拥有成为“职业女性”的空间。也就是说,在古希腊的社会体系中,女性并非全然幽闭,这也是萨拉·波默罗伊在史料中极力寻找出的种种“微光”。书中写道,即使是娼妓,不少也受过教育,拥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类似中国历史上的名妓;即使是无声的女奴,也通过自己的劳动支撑着整个社会的运转。从古希腊到古罗马,贫苦女性需要外出劳动,从事的职业往往是女性家务的延伸,可以成为洗衣妇、纺织工、商贩和保姆等。

雅典娜女神雕塑
古希腊的私人住宅设计,本身就体现了两性隔绝的因素,“住宅内部空间会被划分出专属于男性和专属于女性的区域。女性通常住在相对幽深的房间里,远离街道与房屋的公共区域。如果一座房屋分为两层,妻子会带着女奴住在楼上。”但萨拉·波默罗伊依然书写了女性在这狭窄空间里的努力,比如在离婚案件中展示的独立性。贝塔妮·休斯的《特洛伊的海伦:女神、公主与荡妇》中也有不少相关细节。她考察希腊诸岛后发现,出土文物中记录了众多拥有财产的女性——
皮洛斯出土的一套和土地所有权有关的泥板上,写着两个女人拥有大片土地,其中一个叫卡帕蒂亚(Kapatija,“掌管钥匙的人”),另一个叫埃里塔(Erita,意为“女祭司”)。泥板上列出的那些拥有“onata”(即土地“收益”)的名单中,有半数都是女性的名字。这意味着女性可以是地主,并且有权开发她们的土地。
此外,“在反映自然的米诺斯绘画中,无处不在的是女性,掌管一切的似乎也是女性。而且可能因为如此,其他米诺斯图像中的女性也获得了极大的尊重。克诺索斯有一幅损毁严重的壁画,在伊拉克利翁博物馆中也被称为‘游行壁画’,上面画着一名坐着的女性,她可能是化身为高级女祭司的女神,正被一群爱戴她的男女簇拥着。信徒们倒退着走,以示对这位衣饰异常奢华的人的尊重。”女性甚至掌管着至关重要的粮仓:“掌管着大自然的食品柜的,将永远是一群可爱且不会擅离职守的女人。女人很重要,或许是因为她们拥有某种特权,洞悉自然的奥秘和灵性的世界……”
古希腊和古罗马对女性的压制和些许“放松”,侧重各有不同。从《女神、娼妓、妻子与女奴》一书的书写来看,希腊在社会生活层面对女性的限制更多,不管照顾家庭还是生育,抑或是被供奉于神庙,女性都在满足男性的需求。作为妻子的古希腊女性,在法律上几乎全无保障,但却要通过嫁妆制度维系家庭经济,通过宗教仪式维系城邦信仰,还要承担教育子女的重任。罗马则很少像希腊那样在文学层面赞美女性,但罗马女性拥有更多实质自由,可从事行业更多,而且因为罗马帝国的四处征战,男性远征后,女性在公共生活中的出现频率远远高于古希腊各城邦,贵族女性甚至可以参与政治角力。虽然女性不会得到任何公职。当然,即使如此,她们依然没有多少独立性,比如古罗马贵族男性的炫富,往往通过妻子的服饰来展现。
女性权利的争取绝非现代社会的产物
要理解《女神、娼妓、妻子与女奴》对古希腊和古罗马女性的书写,不能不了解作者萨拉·波默罗伊的人生。1938年出生的她,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但在就读期间,她所在的古典学系并无女性教员。她在得克萨斯大学开启教职工作时,是系中唯一女性。受聘于纽约市立大学后,她亲身经历了性别导致的不公正待遇。她对古典女性的书写,实际上也是对现代女性的捍卫。萨拉·波默罗伊认为,女性权利的争取绝非现代社会的产物,而是古已有之的复杂博弈。从这一点来说,古希腊和古罗马如此,中国古代同样如此。
近年来许多人对宋朝极尽吹捧,认为这一时代开放包容,人们拥有更多权利。他们绞尽脑汁从宋朝的种种细节中寻找“闪光点”,以此作为佐证。宋朝经济发达,女性嫁妆相对更为丰厚,尤其是中上阶层,这一点就被一些人鼓吹,认为嫁妆为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提供了经济后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抗父权制。
但美国学者伊沛霞在《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一书中写道:“嫁妆在后来遭到的限制多半也始于宋代,因为宋代的儒家学者在女人要求和使用嫁妆的问题上流露的感情比较复杂。比如司马光谴责女人把嫁妆视为私人财产以后带来的隐患;他对家庭的看法,侧重于把它视为共财的团体,而这样一来就有了基本的矛盾。如果财产对家庭如此重要,那么家长宁愿儿媳带来丰厚的嫁妆,而且陪嫁多的媳妇就会比少一点的妯娌更受公婆的欢迎。司马光希望用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解决这个结构性问题:公婆不应该贪婪;新娘子不应该狂妄傲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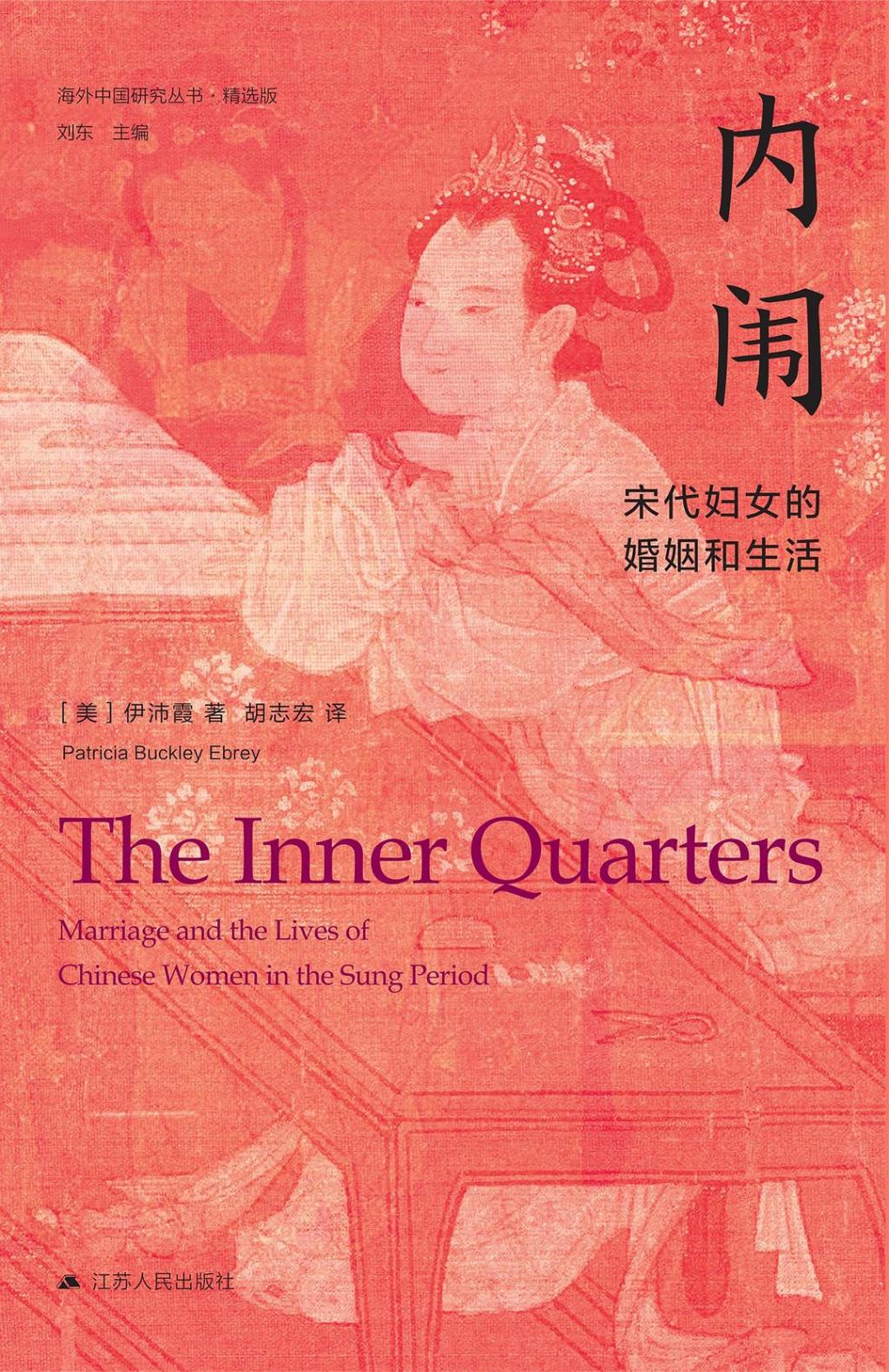
《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
在司马光之后,还有对女性财产更为激进的限制方法。程颐等学者号召恢复更纯粹的儒家祭祖礼仪,一般认为,其动机在于与佛教展开竞争,也在于士人阶级发展祭祖仪式以适应自己新的社会和政治地位的需要。但“经过一个过程,人们才慢慢看出来这些针对妻子财产权的想法。朱熹在《家礼》里引述司马光的观点,主张防范妇女因私人财产得到过度的权力。朱熹也像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赞扬把嫁妆用在丈夫家庭的妇女。与此同时,他在《小学》里指出,来自于地位不高、财产不多的家庭的妻子们更好一些,因为她们更容易适应从属性家庭成员的地位。”换言之,宋朝女性并未因为嫁妆丰厚而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而是恰恰相反,那很可能是噩梦的开始。这一点与萨拉·波默罗伊的书写有相通之处,尽管古希腊的嫁妆制度和宋朝有所不同,但其核心目的是一样的。
再举一例,宋代妻子吃醋的事情特别多,有人就认为这是女性权利的彰显,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在中国古代,男性纳妾是寻常事,妻妾间其实是主仆关系。但因为古代婚姻制度自身的缺陷和婚姻的本质,夫妻更像经济上的合伙人,在情感上,丈夫很多时候会倾向于因情欲而结缘的妾。宋朝确实有不少著名的吃醋事件,奸臣王钦若就特别怕老婆,不敢纳妾。秦桧权倾朝野时,妻子将他怀孕的妾室卖掉,他也无可奈何。司马光为何曾经提倡妻子应控制嫉妒情绪,认为嫉妒是极其恶劣败坏的行为?一是为了维护男性,二是因为这种现象在当时确实不罕见。但这事儿能怪女性嫉妒吗?又真的能归结于宋朝的开放吗?显然不能。因为妻子对妾室的嫉妒,本身就是基于尊严,基于自身为家庭付出未得到回报的现实。而这个土壤,本身就是对女性不公平的——将女性在不公平的大环境里所做的有限反抗,视为“大环境的开放”,这不是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吗?
如果研究当时的女性面相,就会发现非常模糊。女性则责任在于相夫教子,她需要成为好妻子、贤内助、慈母和孝媳,但唯一失去的角色恰恰是女性本身。同时,妾在当时被视为商品,可以随意转赠,命运普遍也相当悲惨。实际上,宋代是“妇女的处境和地位明显恶化的时代,缠足的盛行、杀婴现象的存在、寡妇殉节的增多、理学家对女性的进一步禁锢等,似乎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和强化着这一印象”。尽管因为经济的发展,宋代女性的经济条件要更好一些,但面临的境况却实在糟糕。《女神、娼妓、妻子与女奴》中的古希腊女性同样如此,她们被要求忠贞,却不能阻止丈夫寻花问柳。她们的责任就是相夫教子,被赋予许多责任,但唯一失去的角色同样是女性自身。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