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只要一工作就读不进书了?”这不仅是很多人在离开校园进入职场后会发出的感叹,也是日本评论家三宅香帆于去年推出的一本新书的题名(日语原题:『なぜ働いていると本が読めなくなるのか』)。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日本似乎是一个“读书大国”:公共交通的乘客有相当大比例的人手捧图书而不是电子器械,而实体书店也没有被电商和数字出版挤压到喘不过气。这些现象可能是事实,但与此同时,在人口高龄化的冲击之下,日本出版业也在不断萎缩。在每年秋天都会举行的“读书推进月”活动中,国民对于书籍的远离(“本離れ”)几乎是铁定会登场的“老生常谈”。根据日本文化厅最新的调查显示,在2023年一个月内读不到一本书的民众有62.6%。这比五年前的数字增加了约15%。认为自己的读书量比之前减少的人更是近7成。同时,日本全国的纸质出版物总价在1996年达到了顶峰的2兆6564亿日元,而今天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了原有的四成水平。
有意思的是,在日本人越来越不阅读的大背景之下,三宅香帆关于大家为什么不读书或者说读不进书的著作却意外受欢迎。该书的销量突破了30万本,甚至拿下了包括2025年新书大赏在内的数座奖项。那么作者是如何解读现代人特别是工作后的“社会人”为何不读书的?而在日本发生的这一切对于其他国家又有何种启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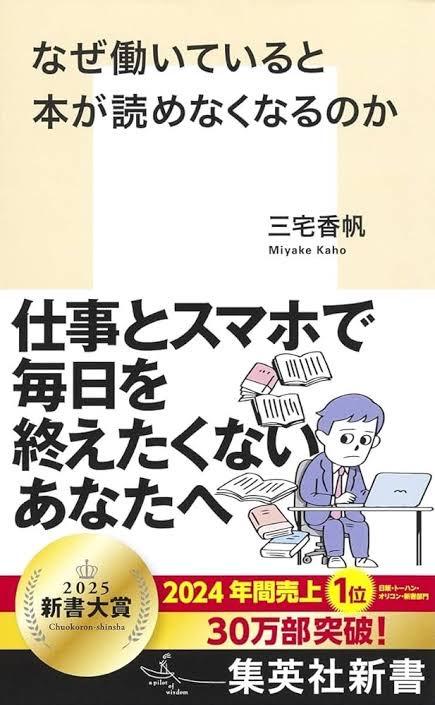
三宅香帆《为什么只要一工作就读不进书了》日文书封
读书与工作的近现代史
《为什么只要一工作就读不进书了》的设问十分具体:作者想要探讨的不是宽泛的“为什么大家不读书”,而是为什么“在进入职场后”的大家无法再认真地读书。一个直觉式的回答可能是: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啊。对此,作者追问道:那为什么我们可以继续在下班后看似无负担地上网、游戏或短视频呢?在书中,作者三宅事实上把核心的问题进行了反转:为什么在此之前的人们会一边工作一边阅读呢?而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就需要回溯自近代以来日本社会中读书和工作关系的发展史。
在近代之前的日本社会,自然也存在着书籍和读者。不管是平安时代带有宫廷色彩的《源氏物语》还是江户时期更贴近庶民的市井故事,都展现了写作和阅读所取得的成熟发展。但就像其他器物或思想一样,现代意义上的“阅读”在明治维新之后才逐渐成形。而它之所以成为可能,和读书行为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密不可分。从内容上来说,以二叶亭四迷为代表的作家发起的“言文一致”运动,让一种更贴近日常对话的文体成为了写作的主流。这大大降低了阅读门槛。从形式上来说,近世的阅读更强调旨在发出声的“读”。读者们在以学堂为代表的场所进行着一种“公共式”的朗读。而到了近现代,一种以“阅”为基础的“看书”成为了更为普遍的选择。而这种“默读”的行为也让一种更为私人化和效率化的阅读成为了可能。另一方面,阅读的发展又和制度的演进密不可分。在“文明开化”的旗帜之下,明治政府十分重视大众教育。图书馆这一现代场所也开始在全国普及。三宅引用数据指出,在日俄战争结束后的十年,日本公共图书馆的总数实现了四倍的增长。这无疑更进一步地降低了阅读的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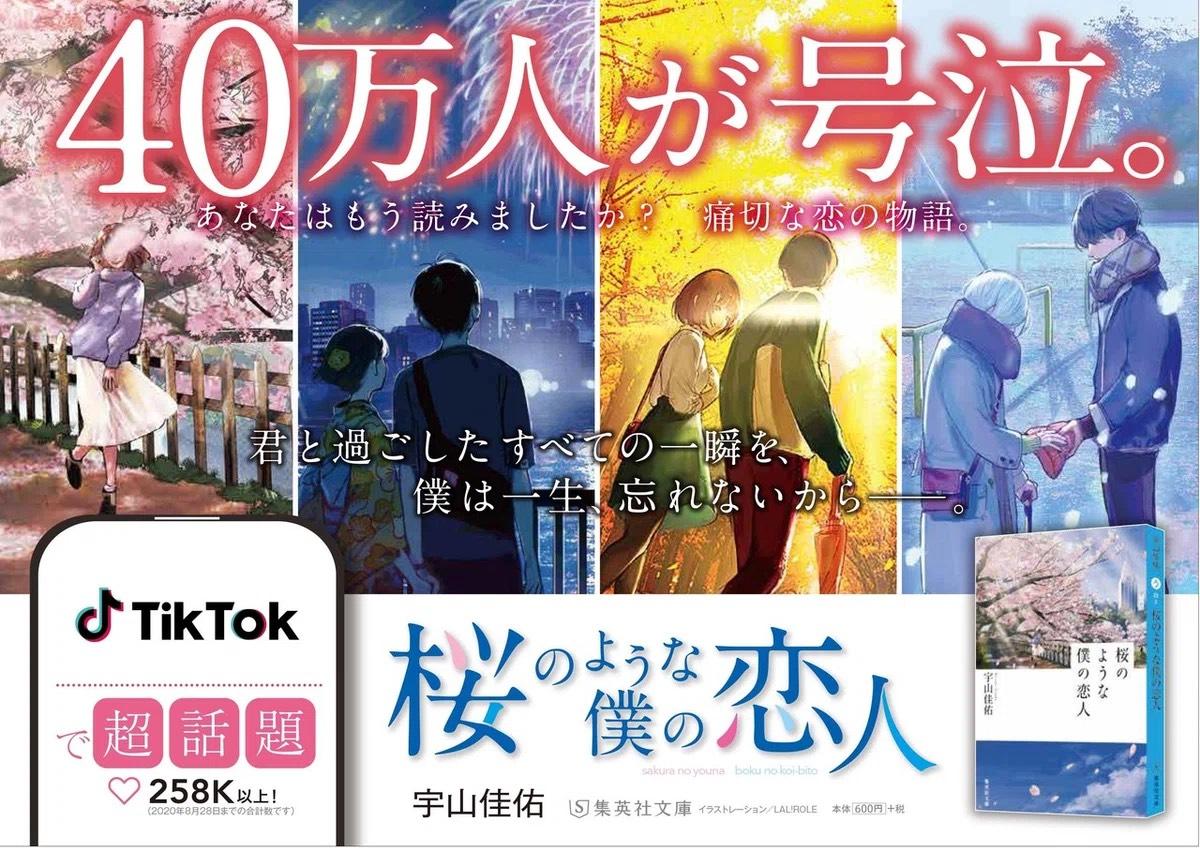
日本书商积极地拥抱新媒体并以它们作为营销手段。图为集英社《我的樱花恋人》一书的宣传海报。图左特别注明了该书在TikTok上有25万多人按赞。因为社交网站带来的流量,该书的销量突破了70万,并被改编成Netflix电影。
比如从2020年左右开始,一个以话题#BookTok为核心的虚拟读书社群出现在了海外版抖音TikTok之上。截至去年10月,此话题累计获得2090亿次的播放以及5200万次的投稿及转赞评。社交网站的用户(绝大多数是年轻人)用一种和以往阅读评论不一样的“快消”方式介绍图书并且和其他读者产生连结。而新媒体的巨大传播力度也促进了年轻人重新回到阅读之中并带来了巨大商机。一个最好的例子是美国作家Colleen Hoover。她的一系列小说在2021年左右被TikTok的网红发掘并引发巨大讨论。2022年,全美畅销榜中她的作品有六部入选。在此之前,她的许多小说甚至是靠着自费出版的形式才得以问世。2023年,她还成功入选《时代》杂志影响全球100人的名单。在此势头之下,包括企鹅书屋等老牌出版公司也开始在自己的市场营销中积极引入社交网站。类似的利用新媒体来推动阅读的事例在日本也同样可以找到。思想市场曾经介绍过围绕着网红Kengo所展开的一系列论争。他在短视频里介绍的图书大受欢迎并屡次加印,但同时也引来了“文学批判”建制派们的不满。在短暂休整之后,Kengo重新恢复了关于小说介绍的投稿,我们也可以很明确地发现出版社对于其活动的赞许与支持。
日本另一位文化评论家饭田一史在研究了国民阅读的调查数据后指出,虽然总体上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但进入2020年代后初高中生们的阅读量与频率其实并没有明显减少甚至有部分好转。而他们也是受到TikTok或X等社交平台影响最大的族群。虽然无法直接断言是社交网站提高了年轻人的阅读量,但至少可以肯定“新媒体”并不直接导致人们“读不进书”。归根结底,不管是上文提到的全集或者文库本在内的各种出版形式,其实在某个历史时点也是一种“新媒体”。重要的是,如何在一个变动的环境之下寻找到一种更为适合的阅读方式。这当然是每一个读者的责任,更是宏观的社会/制度的责任。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